今年年初,迟子建带来了新作《东北故事集》,其中收录了《喝汤的声音》《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碾压甲骨的车轮》三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都在东北。很多读者熟悉迟子建是从她的长篇代表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开始。1964年隆冬,迟子建出生在中国大地的最北端——漠河。故乡东北,始终是其创作的母题。

她曾在采访中说:“我的出生地漠河,包括我现在常回去的地方,至今仍然是中国的边疆,经济欠发达,但自然无比壮阔。命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四季如此分明,能够感受漫长冬天的地方,使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感伤的东西。当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痛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触及文学一些本质的东西了。”
读迟子建的文字,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生长的那方土地、对每一个世俗的日子恒久的爱,执着地贯穿于字里行间。她甚至常常在梦里遇见大自然的景象,她怀着又敬畏又热爱的心,不由自主地书写这些真正不朽的事物。记者舒晋瑜曾采访迟子建,全面回顾了她的创作生涯。这篇访谈被收录进舒晋瑜的《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篇幅原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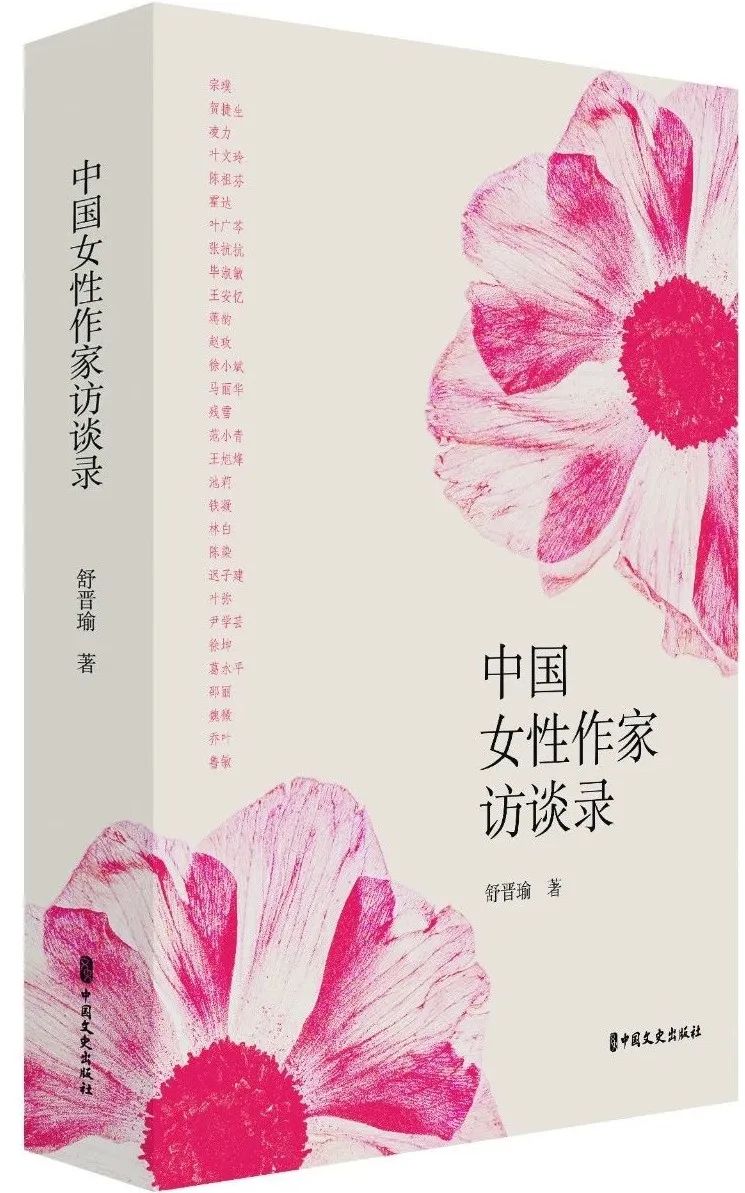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舒晋瑜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1月。

喜欢上一个题材,
如同喜欢上一个人
舒晋瑜: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童年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迟子建:小时候我是在外祖母家里长大的,那是个广阔空间, 感觉人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 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1985年,黑龙江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看看,这像不像小说?
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 一下。即将出发前,朱伟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就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莫尔道嘎》(2020)剧照。
我的写作是从大兴安岭师专开始的,那时课业不紧,我大量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并开始悄悄地写作,毕业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一个。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14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
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
好在这3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10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做了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
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的东西。
舒晋瑜:关于“伪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伪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伪满洲国》,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8月。
迟子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感到刺耳,仿佛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14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脚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
计划写40多万字,实际上写了60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 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 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伪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写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沉浸在“满洲国”的氛围里,傍晚走在街头,感觉调子都是灰的。
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其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我觉得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写《伪满洲国》,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

我想写出人类文明进程
中的尴尬、悲哀与无奈
舒晋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使您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作品像一面镜子,照耀着那些远离山林和自然的灵魂。但是单纯地把这部作品理解为历史小说,也失之偏颇吧?
迟子建:是的。我去追踪这个部落的时候,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但他们的生活快乐。他们从不乱砍滥伐,打猎也决不滥杀,够一周的食物就行了,不过多索取,在知足中产 生富足感,他们唱的歌旋律优美——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是有益的启示。
舒晋瑜:看到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族、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反思现代生活和原始生活的冲突,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用意?
迟子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部落变得和我们一样呢?我们为了所谓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本身就是一种粗暴。不仅鄂温克这个部落面临如此境遇,世界上其他少数民族也面临这个问题。
那些有自己生命信仰的弱小民族,在现代文明面前面临的生存艰难和文化的尴尬,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太贫血了,所以当真正的鲜血喷溅时,我们以为那是油漆!

纪录片《最后的敖鲁古雅》(2017)剧照。
舒晋瑜: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说,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
迟子建:我不会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额尔古纳河右岸》其实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延伸,不同的是,写作这部长篇时激情更为饱满,大约触动了我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其实写它是有难度的,首先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鄂温克老女人,其次,我要在一天中把近百年的故事讲完。好在我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的生活习性,写起来没有吃力的感觉。
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
舒晋瑜:《白雪乌鸦》以1910年冬至1911年春哈尔滨暴发鼠疫的历史作背景,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枝缠叶绕。起意写作《白雪乌鸦》有什么原因?书名有何寓意?
迟子建:2003 年“非典”,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哈尔滨的媒体报道说,这与100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完全一样。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020)画面。
我查阅了资料,1910年鼠疫时,2万多人的傅家甸(也就是哈尔滨道外区)竟然有5000人死于鼠疫!我开始留意这个事件,留意伍连德,但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他这个人物。我想知道鼠疫突来时,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另外,当年老哈尔滨的社会状态我也特别感兴趣——中东铁路兴起没多久,有8万俄国人和几千个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城市里有很多西式建筑,剧院上演的是芭蕾舞、西洋戏剧, 而傅家甸则是尘土飞扬的流民区域。如果把鼠疫放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写出这段历史,会很有意思。
在生活中,我偏爱黑白色,它们对比强烈,也是最能与其他颜 色达成和谐的色调。哈尔滨的冬天,最常见的是白雪,长达半年的冬天,使雪花成了从天庭来到人间的常客;而乌鸦在满族人的心目中,是。
传说乌鸦救过清太祖,朝廷里特设“索伦杆”,祭祀乌鸦。而这场大鼠疫之后,清王朝就灭亡了。而我在查资料时也看到,当年的哈尔滨,尤其是松花江畔,乌鸦很多。我觉得黑白色调特别契合我这部长篇小说的气氛,所以就用《白雪乌鸦》作书名。

我的女性人物是
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
舒晋瑜:《晚安玫瑰》中,景物的描写由大自然转移到城市,在露台、在屋顶、在高窗上。当您笔下的舞台转移到城市,心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迟子建: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描写的露台、高窗、坡屋顶,这样的房屋基本都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那一带,那里被誉为“哈尔滨建筑博物馆”,都是历经沧桑的老建筑,各种风格的,是个露天艺术长廊,我的笔徜徉其间,一样滋润!
因为我把这样的建筑当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能够活在这样的屋檐下,比活在一个模式建造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群中,要曼妙得多!当然,我的笔也抒写都市里的 狭窗陋巷,抒写像《黄鸡白酒》的小酒馆,它们在我眼里充满了世俗烟火气,一样是动人的风景。

《白雪乌鸦》,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3月。
舒晋瑜:《白雪乌鸦》《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单看书名就是诗意并且色彩绚烂的。是有意为之?
迟子建:没有。也巧了,这3部抒写哈尔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标题都是4个字的。《黄鸡白酒》,它来自辛弃疾的词“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辛弃疾是我最喜欢的词人。 至于《晚安玫瑰》,原来并不是这个篇名,是发表的最后一刻改的。
舒晋瑜:《晚安玫瑰》借着描写小娥的爱情,折射了中国百姓的生存状况、买房的压力、婚姻的矛盾甚至亲情的悖离……我很感兴趣这个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心态?您对这部作品比较满意,满意在什么地方?
迟子建:写作《晚安玫瑰》,差不多花掉3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的命运的影响。这里的两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后裔吉莲娜和报社校对员赵小娥,都有“弑父”行为,所以最早篇名是叫《弑父的玫瑰》。
编辑们觉得 “弑父”二字放在篇名太直露,所以我最后改成了《晚安玫瑰》。我 对它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对这两个女人的塑造。她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是复杂的。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020)画面。
舒晋瑜:《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酋长的遗孀,《黄鸡白酒》有春婆婆,《晚安玫瑰》有吉莲娜, 您在描写笔下的老女人的时候,是否有格外的感情?
迟子建:我希望自己也能活到她们那般年纪,宠辱不惊,宁静如水,朴素地活到人生的夕阳时分。
舒晋瑜:您作品中的任何女性,几乎都具备健康、不屈、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果有迷茫,肯定也会在某种寻找之后豁然开朗。我想这跟您本身的性格也有关系。您能总结一下作品的女性人物吗?
迟子建: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什么样的,男性人物又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如同一场戏,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
我想我写过的女性人物,最典型的特征,应该是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不过让我细致地“总结”她们,我还是很吃力。因为在“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 跟让我登珠峰一样难。

写作帮我度过
人生的难关
舒晋瑜:中短篇的写作,其实一点都不亚于长篇所耗费的精力和心思。您确定体裁时,以怎样的标准判断?
迟子建:作品“容量”的大小,决定着体裁的长、中、短。比如我收集《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我就知道,手中握着的,是长篇的种子。因为它容量大,张力大,可塑性强。可是像《清水洗尘》《逝川》和《亲亲土豆》那样的题材,它出现时,就是短篇的姿态。
相反,类似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起舞》这样的小说,我打腹稿时就知道它会以中篇的形式出现。容量大的水流,你把它注入窄小的河床,它就会泛滥成灾;而你非要把一条小溪引到大河的河床上,水流活跃不起来,势必会成为死水。所以,把短的东西拉长是臃肿乏味的;而长的东西,你想遏制它的生长,也是不可 能的。
舒晋瑜:故乡在您作品中的呈现,或者说故乡与作品的关系,这么多年来有怎样的变化?写《北极村童话》时那么清新天真,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白雪乌鸦》,已经具备了史诗般的厚重。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020)画面。
迟子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当一片土地由亲切变得相对陌生的时刻,那么拷问作家良心的时刻便也到了。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和锻炼。
从《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黄鸡白酒》,毕竟相距 20 多年的时光。创作初始的那种恬淡和忧伤,我至今迷恋着,也许那是我与生俱来的气息。我并不特别清楚写作的变化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就像我不知道,眼角的皱纹,究竟是哪个时刻悄悄爬上去的。
舒晋瑜: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对自然景物都有非常细致的刻画,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像涓涓细流融入故事。这种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描写,在当代作品中越来越少了。似乎大家都没有心思去关注周围的景物了。您的这种风格,是来自俄罗斯文学的熏陶,还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
迟子建:最主要的是生活环境的影响。你想啊,我出生在大兴安岭,17岁之前,都没出过山,满眼看到的是大自然的风景。那里人烟稀少,四时景色不同,所以从童年起,我等于在看老天绘制的一幅幅风景油画——春日森林的嫩绿,夏日林间缤纷的野花,秋日五花山的绚烂,冬日冰河的苍茫,还有那沼泽上的水鸟,林间的溪流,变幻无穷的天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想起故乡,往往就是这一幅幅诱人的风景图画。每当写到故乡,这样的风景自然而然从笔下流淌出来了,因为我小说的人物就活在这样的风景中。
舒晋瑜:回顾30年的写作,您愿意作何评价?
迟子建:1983年我在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到手中的笔,会这么让我不舍,一直到今,还牢牢在握。写作帮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那个源自现实,又与现实有着不一样气象的天地,它是那么令我着迷!
我早期的作品,确如评论家所说,是纯净忧伤的,而近期作品,有了苍凉之气。我想这与我对文学的认识的加深和人生阅历的增长有关。但我所有的变化,都是渐变,而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所以对自己的写作,我也很难划分明确的阶段,因为创作是有延续性的。
我有个习惯,就是作品发表之后,再读上一遍。我读它是为了给自己找不足。我在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不足,所以总是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可下一部作品出来后,我读后又发现了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我想或许我未来还能写得好一些。从生活的意义来说,写作帮我度过人生的难关,我爱人离世后,是这支笔给我强大的支撑,为此我要感谢写作。
舒晋瑜:您曾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从萨满治病的禁忌(不许点灯)、萨满跳神的服饰(彩色神衣)、法具(神鼓)、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除岁奇迹般地好了)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
迟子建:大自然确实有股神秘力量。我在收集《额尔古纳河右岸》 资料时,知道有的萨满在跳神时,能把大地踏出一个坑来。超自然的力量,是我们所不知的。而我小时生病,家长也用“烧邮票”的方式给我叫过魂。
我去北京天文馆参观,看着陨石展厅中一颗微小的来自月球的岩石,我总想夜晚时它会不会发光,它会不会是嫦娥舞蹈时,衣裳落下的一颗纽扣呢?科学可以探明宇宙的奥秘,但对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科学也无法解释。其实世界有谜团是好事, 我们对世界还有敬畏之心。
舒晋瑜: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在写作中,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诉求?
迟子建:悲天悯人的前提,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的风景。 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会把“根”扎 得很深,不会被鬼魅劫走。

《东北故事集》,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
舒晋瑜:智障人物也是您作品中的常客,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类的人物身上,您发掘出他们纯净的思想、奇异的智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第三地晚餐》中陈青的哥哥陈墨是个遭人嘲笑的智力欠缺的人,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 这样的人物,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会出现,包括世界名著。
迟子建:我的短篇《采浆果的人》,也写了智障的人,这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我们小镇不大,但有好几个智障的人,他们在我眼里不是“傻瓜”,而是有光彩的人。他们不循规蹈矩, 说出的话永远满怀天真,他们在一种“天籁”状态下生活——虽说那是病态的。我总想,我们觉得他们可笑,可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可笑。
舒晋瑜:但凡写作者,总希望突破。您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每次动笔之前,会在哪方面着力更多?
迟子建:如果说素材是柴火的话,当你准备了高高一摞柴火后, 最希望找到火种点燃它。这个火种就是形式。找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是着力最多的。比如我的几部长篇,《伪满洲国》14年的历史太庞杂了,如果面面俱到,4卷也可能写不完,最终我采用编年体,60多万字完成了它。
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当资料做得完备后,就是找一种最理想的方式表达它。结果我采用 一个老女人的自述方式,以一天中的3个时段来讲述故事,整个素材就被点燃了,写起来非常顺畅。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舒晋瑜;摘编:荷花;编辑:王菡;导语校对:穆祥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